楊易,1946年生于廣東省電白縣。現為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學部委員、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文學圖集》、《中國敘事學》、《文學地理志》、《還原魯迅文化血統》、《魯迅作品精粹(選評版)》三卷本、《國學研究會志》等50余部著作,發表論文500余篇,計1000余萬字。主編著作16部,70卷本。

全部都是數據圖片
去年冬天,我以古今文獻、碑刻文物、野史雜著、風俗信仰、地域基因、當代思想、魯迅深厚的人生體驗等豐富扎實的材料,從魯迅的文化血脈、哲人視野、愛國情懷、巨人智慧等多個角度,評述了220余篇文章。這其實是對五四前后半個世紀文化精髓的注解,是對20世紀最深刻的思想和文學巨匠之一全方位的解讀。以一人之力做如此有挑戰性的事情,正如《詩經》所說:“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現在我提出這些評述,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評指導。
魯迅研究是我學術研究的起點。從1972年在北京西南郊的一個工廠倉庫里讀完十卷本的《魯迅全集》,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唐濤、王世敬,開始系統地研究魯迅。此后,我發表了一批有關魯迅的文章,創造了個人學術生涯中不少“第一”。1981年上半年的《論魯迅小說的藝術生命力》是我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1982年7月的《論魯迅小說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征》是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1984年4月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小說綜合研究》是我的第一部學術專著。
我邁出的學術第一步,是我研讀《中國現代小說史》、勤于探究中國文學從古至今乃至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的淵源與精髓的第一站。選擇這一站作為學術思考的起點,在與魯迅進行思想文化與審美精神的深度對話后,再準備繼續前進,對古今敘事、歌謠詩詞、國史志、諸子百家的學術著作進行了長途奔襲。應該說,這積累了寶貴的思想批判能力、審美體驗能力和文化還原能力。經過三十余年在審美文化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耕耘,我回過頭來,重新梳理魯迅的經典智慧與文化血脈。 近兩年來,我陸續推出了《恢復魯迅的文化血脈》(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遙遙致敬漢唐——魯迅與漢畫像石》(《學術月刊》2014年第2期)和三卷本的《魯迅作品精粹(選評版)》(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8月),徹底梳理了我學術生涯第一站的存量。整理的結果讓我對魯迅思想和文學的存在深感敬佩和感激。有了這個標桿,人們在思想和學術上就不能懈怠了。

最近,我將這三份共一百三十三萬字的材料進行了校對,并根據校對的內容寫了兩篇文章:《魯迅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和《怎樣推進魯迅研究》,每篇兩萬余字,前者還處于草稿階段,文章寫得倉促而粗略,只是為了梳理一下近幾年回歸魯迅的精神軌跡。
魯迅給我們留下了什么?過去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們常常會列舉一系列魯迅的觀點。不如換個角度,想想魯迅在精神品質和思維方法上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啟示。觀點是具體的,很容易隨著歷史的進步而獲得或消逝;精神品質或思維方法則具有潛在的普遍性,運用得當,可以進入新的精神過程。
嚴肅而深邃的目光
魯迅寫了33部小說,其中16部提到了“眼光”。《奔月》中,易“挺拔如磐石,雙目直射前方,在巖石下閃如閃電,須發散開,飄動如黑火”,這被視為人物精神的鑰匙。《取法》中“要用腦子,睜開眼睛,自己去取”。《紅洞花女·小導論》說,對于《紅樓夢》來說,“光是意義,就因讀者的眼睛不同而有各種解讀:儒家看到了《易經》,道家看到了情欲,才子看到了纏綿,革命者看到了反滿,八卦者看到了宮廷秘聞……”可見眼光是認識世界的鑰匙。 如清人吳喬在《爐邊詩話》卷六中說:“讀書時,不可只看紙的表面,須看紙的背面。”
每本《魯迅作品精粹(選評版)》里,都有我寫的書簽:“讀魯迅,能使心靈的眼睛明亮如巖石下的閃電。”重點也在于“眼光”。香港版《魯迅作品精粹》的序言也說??:“我們在觀察中國事物的時候,總能感受到他那銳利、嚴厲、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所展示的、所譴責的、所期盼的。” “魯迅的視野,成為20世紀中國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成果,這種成果超越了封閉的儒家精神體系,對于現代中國文化體系的建構具有實質性的意義。魯迅的同時代人中,有比他更激進的,如陳獨秀;有比他更機智的,如胡適;有比他更風趣的,如周作人;但沒有人像他一樣看透中國歷史進程的深層本質和中國的生活模式,這使他的作品更值得一讀再讀,越嚼越香。魯迅學思深,思考深,觀察深,表現出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流的思想洞察力、歷史洞察力和社會洞察力,使他的學識淵博、閱歷深厚,形成了一種具有巨大穿透力的歷史通識。”
比如解剖國民性的命題,《阿Q正傳》寫阿Q的革命:阿Q夢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甚至把自由黨誤認為“柿油黨”,取而代之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榜》等小說和地方戲《龍虎斗》中的各種武器,如平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雙刃劍、鉤鐮槍,成為他想象中的成群搶劫的家伙,帶有民間狂歡的諷刺意味。魯迅的眼光看透了群體的潛意識。魯迅有一個深入人心的發現:“暴君的反面就是奴隸南陽文學藝術網,有權的時候可以為所欲為,失了權就變成奴隸。” (《南言北言·諺語》)這是魯迅的眼光,認為魯迅解剖國民性是受西方傳教士影響的“殖民思想”,是脫離事物本質或將事物本質虛無化的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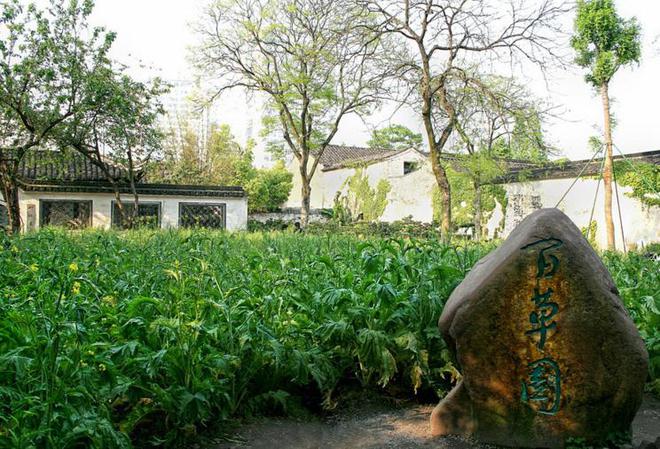
令人耳目一新的智慧
香港版序言也說:“誰能想到,魯迅只用一支小小的廉價的‘金’筆,就能如一陣風雷般掀開古老中國的厚重帷幕,賦予受苦受難的靈魂以神圣,讓一縷晨光透進暴風雨的云層?他對黑暗的重量有充分的估計,一踏入文壇荒野,就立下期望:‘我肩負傳統的重擔,把黑暗的大門緊扣在肩上’,讓青年一代‘去往寬廣光明的地方,從此快樂地生活,理智地行事’。”這賦予了新文學運動以勇者的性格和智者的風范,很難再找到另一位像他一樣了解中國的作家。啟蒙的手術刀如此鋒利,可以輕易批判奴隸制與專制互補的社會心理結構,甚至小辮子、臉蛋這樣的形象,國粹與現代性這樣的話題。野史,將國民性剖析得淋漓盡致。讀魯迅,可以體會到一種苦中之樂,即一種既不痛苦也不快樂,而是奇異地痛苦和快樂的大智慧。在智慧的境界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他“睜著眼睛看”面對現實的人生態度,以及他向“漢唐之勇”致敬、提倡“取其所用”的豁達。他晚年所運用的唯物辯證法也活靈活現,絲毫沒有“論匾短視”的隔閡(見其《辯》)。在他對家庭、社會、時代、父與子、女性,以及文學與革命、知識分子與人民、圣人、名人與真理等問題的深思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常識的融合,感受到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智慧和禪意。 他擅長諷刺,但他的諷刺立足于民眾精神,冷酷包裹著熱情,以一種“冰與火”并存的特殊風格,逼退了復古墮落的荒誕,逼出了“中國的脊梁”和“中國人的自信”。魯迅使中國人對自身本質的認識達到了新的歷史深度。正是這種充滿奇異痛苦和喜悅的歷史深度,為百年改革事業注入了類似于“路人”的不懈精神動力。
魯迅的散文得益于他的博學。民初的魯迅是一個獨特的精神存在,他用沉默來排解痛苦,用沉默來磨練內心的力量。對精神痛苦的治療,使思想者真正深刻地品味到了文化的韻味。如果沒有民初對古碑刻的研究、對佛經的抄寫、對漢畫像石的收藏,就不會有魯迅這樣深厚的精神深度,不會有對中西文化精髓的深刻領悟。魯迅的人文情趣十分廣泛,他年輕時不愛刺繡、不愛民間戲劇,但喜歡古碑刻、漢磚木刻,這些都讓他體會到了文化情趣,體會到了古人的心靈。魯迅作為作家,有著博學多識的文化修養背景。 1925年,他寫出《照鏡隨想》,寫得自由自在,真正展現出博學的風采。散文是魯迅創造的一種共感民族國家苦難的文化方式。
強健骨骼
魯迅是一位睿智而勇敢的啟蒙斗士,他在《自嘲》一詩中寫道:“冷眉頭面對千萬人的批判,我甘愿為兒女當牛。”他的堅硬,來自鮮明熱烈的愛恨情仇的磨煉與淬煉。“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斗,在這詛咒之地,擊退詛咒的時代!”《上吊的女人》寫出了一種“民俗活化石”,甚至可以說是“女鬼活化石”。有“鬼”的化石嗎?鬼本該與“黑暗”和“死亡”聯系在一起,但魯迅卻從中激活了強大的生命力,從而構建了現代中國文學獨特的意義方式和意義深度。
同情和尋求

從1918年震撼人心的《狂人日記》,到1919年含蓄細膩的《孔乙己》,不到一年的時間,魯迅小說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展現了魯迅文學世界非凡而深不可測的深度。在《孔乙己》中,魯迅在家鄉的街頭拾起如風中落葉般飄落的舊日生活碎片,夾在風起云涌的《新青年》書頁之間,由此審視父輩未能成士、未能成官的卑微命運,筆下充滿悲憫。難道這就是他們的“寬廣輝煌,萬物昌盛”嗎?地名、人名,都充滿著諷刺的張力。
文章不僅在思想形式上追求獨創,書中也呈現出獨特的精神探索深度。《吶喊》氣勢磅礴,《徘徊》反思深刻。《祝福》反思五四啟蒙。辛亥革命后近十年,五四風起云涌,但主張理性主義的家叔呂四罵的“新黨”還是康有為。歷史似乎并未因思想的風起云涌而向前發展。《孤獨的人》反思“孤獨”。胡適1918年出版《易卜生主義》,引用易卜生《人民公敵》:“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是最孤獨的人。”經過如此深刻反思,孤獨的魏連書又怎能說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 他只說了一句“我還能多活幾天”,這是魏連書求生意志的宣言,在文中反復回響。在走投無路之時,他成了軍閥杜世昌的謀士網校哪個好,出賣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勝利意味著失敗:“我以前所厭惡的、反對的,我都實踐了,我以前所欣賞的、提倡的,我都拒絕了。我真的失敗了,但我勝利了。”《死的哀歌》沉浸在對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思想文化的反思中,反思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浪漫主義。本文開篇即說:“如果可以,我要把我的遺憾和哀歌寫下來,為子君,為我自己”,為全文定下了悲情的懺悔基調。哀歌來自對年輕知識分子的青春贊頌和對青春逝去的悲哀。 其中,摘錄了一句“被綁蜻蜓的哲學”:“就像蜻蜓落入頑劣少年手中,被一條細線綁住,任其玩弄、虐待,雖然幸好沒有丟掉性命,但最后還是躺在地上,只是早晚的事。”這條逃不掉的細線,是社會風俗、宗法勢力、經濟制度,掌控著青年知識分子的命運。《離婚》反映出啟蒙運動、女權主義之后,鄉村依然被士紳的堂堂主義所主導,壓倒、制約著鄉村原則。七爺神秘的“屁塞”,輕而易舉地推翻了愛姑的“勾刀踢”,是中國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虛無形成”。
關于“如何推進魯迅研究”,我不打算多講了。我認為魯迅是一口大鐘,輕敲則柔,重敲則響;我還是認為魯迅研究還有許多領域和層次的思想、知識、精神文化可以深耕。這取決于研究者舉起的敲鐘錘的材質和大小,以及研究者的知識儲備和思維能力是否與研究對象相稱。我講了推進魯迅研究的五個維度,即更深層次疏通文化血脈、還原魯迅生活、深化辯證思維、重建文化方法、拓展思想維度。
以往魯迅研究的突出特點是注重思潮,特別是外來思潮對魯迅的影響,在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是不言而喻的。但即便過去在探討魯迅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時,著眼點也只是思潮沖擊對這種關系所造成的變化,偏離了文化血統的根本性質。魯迅說:“外在世界雖不落后于世界思潮,內在文化卻仍保留著固有的血統。以今復古,立新宗派,使人生意義深刻,則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便來了,個性便得以拓展,沙之國便變為人之國。”(《墳·論文化的偏向》)他把思潮與血統放在一起,使之對立。 一只手不能鼓掌,兩只手才能鼓掌,才能創造出新的文化宗派,創造生命的意義,創造中國人的自我意識。思潮脫離血統而飄浮,血統脫離思潮而沉沒。重思潮而輕血統的研究只能是“半個魯迅”研究。只有研究思潮和血統,才能還魯迅應有的“深刻完整”。即使研究思潮,也要有血統研究的基礎,才能理解魯迅為什么接受思潮、怎樣接受思潮,怎樣改變思潮的方向和形態。正如魯迅所說:“新主義的宣傳者是縱火者,要有別人的精神燃料才能點火;鋼琴家是鋼琴家,要有別人心中的琴弦才能發出聲音;發聲者是發聲者,也要有發聲者才能產生共鳴。” (《熱風·圣武》)血,是解釋思潮為什么會“著火”“發出聲音”“產生共鳴”的內在依據。
魯迅的文化血脈深廣,深入歷史,涉及民間。從主要支脈來看,魯迅的文化血脈相當突出,從莊子、屈原、嵇康、吳敬璉,從魏晉文章、宋明野史、唐傳奇到明清小說,甚至從越興目連戲、《山海經》、金石學、漢畫像石,都可以找到、把握。 例如,解釋《朝花夕拾》開頭的“狗貓與老鼠”,可以從地域文化和文獻學的角度出發,追溯到800年前,陸游的《劍南詩稿》卷十五中有一首絕句《贈貓》:“裹鹽迎小貓奴,守山房萬卷書,愧對家貧功勞小,寒無氈坐,無魚食。”這是頗為感激貓捉老鼠的功勞。如南宋吳自牧在《紅樓夢》中記載“貓皆人所養,以捉老鼠”;陸游也用貓來表達自己家境貧寒,致使貓受饑寒之苦。 《劍南詩稿》卷三十八有《嘲貓》詩云:“翻鍋何其猛烈,唉,睡不好覺。只思魚不顧老鼠。欲速奔捕蟬,先憐爬樹之輕。衢山何處?此族最有名。”注云:“人言貓為虎之叔,除爬樹外,能教虎百般,又言海市貓為天下第一。”陸游是山陰(今紹興)人,與魯迅同鄉。魯迅幼年所聽故事,與此處“俗語”相符,但魯迅所聽之貓為虎之主,陸游則稱其為“虎之叔”,更添一層親切感。
例如,關于魯迅對藝術的重視,討論的基礎是發現“東方美的力量”。1935年,他寫信給木刻家李華:“我想,如果參考漢代石刻,明清書籍插圖,注意民間所喜愛的所謂‘年畫’,再結合歐洲的新方法,也許可以創作出更好的版畫。”(《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頁)他由此設想了一種新的審美形式:“用這種東方美的力量,侵入文人書齋。”(《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這讓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民國初年的魯迅。 魯迅一生,主要在1915年至1936年這二十年間的兩端,購買了近六千張碑刻、石刻、木刻畫像拓片,成為魯迅文化血脈中重要的思想資源。魯迅從山東嘉祥等地收集了405張漢代畫像拓片,其中大部分是在民初沉寂時期得到的;南陽的246張漢代畫像,是在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間,通過王野秋委托有關人士得到的。 徐壽尚稱贊道:“魯迅對于古碑的整理,不但注重其文字,而且研究其格式……即至于碑文,也考究得十分細致,不用泛泛之詞。”(徐壽尚:《感懷故友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南陽文學藝術網,第40頁)這期間,他曾利用南宋洪適的《禮序》校訂《鄭繼宣殘碑》。在研究古碑時,他多次對清代王昶(字蘭泉)的《金石萃編》作了更正。1915年底,他從北京圖書館分館借來清代黃易的《小蓬萊金石文字》,并抄錄了自己所藏的缺頁。魯迅的金石學和考證學功底,在此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如果沒有如此深厚的傳統學術功底,魯迅不可能寫出《照鏡隨想錄》這樣的散文,也不可能利用山東嘉祥、河南南陽的漢畫像石來審視漢人的生命史、精神史,從中發現“東方美的力量”,并以此來致敬“漢唐氣魄”。只有重視魯迅對外來思想的借鑒,兼顧魯迅根植于自身文化的血脈,才能超越研究“半個魯迅”的境況,還原一個“完整的魯迅”。
“>
 名師輔導
環球網校
建工網校
會計網校
新東方
醫學教育
中小學學歷
名師輔導
環球網校
建工網校
會計網校
新東方
醫學教育
中小學學歷